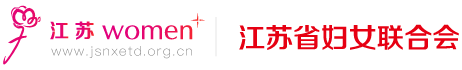天气渐渐凉下来,酱豆子被端上了餐桌。
在同一屋檐下,人们生火做饭,用食物凝聚家庭,慰藉家人。餐桌上那一盘酱豆子,普普通通,凝结着一家人的辛劳和爱。
每年夏天,妈妈都会煮豆子做酱,好像是害怕错过和炙热阳光的约定。
做酱最主要的是豆子。精挑细选的蚕豆在冷水里泡一夜,最硬的褐色外层就可以轻松褪去。之后放水里煮,这时候的火候、时间必须精细把握,我们家喜欢吃稀点的大酱,就需要把豆子煮得软烂些,再出锅去壳。
每每剥壳时,妈妈就把小板凳摆好,我们俩默契地边聊天边从水里捞豆子,撕开一个小口指腹间一挤,蚕豆米就出来了。这一挤就是一下午。门外大树叶子摇曳不停,蝉鸣不歇,等我们终于完工,石榴叶子也已经被骄阳晒蔫泛出红褐色,妈妈把豆壳倒在石榴树根下面,给它施施肥,希望今年能多结几个石榴果。
剥好的蚕豆米要经历奇妙的蜕变:发霉。这可真是一项奇妙的发现,古时候的人们知道豆腐发霉变成臭豆腐还能吃,豆子也能发霉变成酱。
但不是随随便便就让豆子长霉,干燥环境下形成的霉菌才是好菌。妈妈先给豆米裹上面粉,铺在竹编筛子上,上面再覆上端午时节晒干的艾草。
看好的晴朗天气果然没有失约,几天后柴火棚上的蚕豆长了层层霉菌,掀开来已经有了淡淡的香味。
这时候老爸就登场了。老爸的做酱技术未必比妈妈高超,两个人为此总要争论一番,但是大家心照不宣地把体力活交到老爸身上。他烧开一锅水,取出柜子里的陈茶叶倒进去翻滚,茶叶在搅拌下舒展开,水也从绿色渐渐变成黄色,厨房里弥漫着茶香。
沸腾的热水有了味道,大概十分钟后,失去汁水的茶叶被捞出来。等茶水彻底冷却,老爸就要下酱了。将发了霉的蚕豆米平铺在酱缸下面,随着茶水一次次拌进去,豆子被稀释变得黏稠发黄。最后一点茶水倒进去,老爸已经累得满头大汗,他总会开玩笑:“知道我没加盐,汗就要掉进去了。”我也哈哈大笑:“每年你都是这么说的。”
夜幕降临,我们抽空吃完晚饭,再洒好盐水,酱豆子在缸里终于有了雏形:豆米结在一起裹上黄色汁水,变成一粒粒泛着泡泡的疙瘩漂在酱缸里。
今年的酱豆子工作告一段落,接下来就交给时间和温度。
属于父母的烦琐结束了,后面大多是我的任务,要每天不停调换酱缸位置,让酱豆子充分沐浴阳光;下雨了及时端回家,淋了雨,豆子就酸了。
日晒烈阳,晚露夜霜。大约半个月后,不用凑近就能闻到浓郁的酱香,那是属于蚕豆厚重的底味,以及融合了茶叶的清香,又经过缓慢发酵形成的特有味道。老爸说再多晒几天还能做酱油呢。
酱在晾晒过程中是不能搅拌的,小时候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,拿着筷子往里挑,结果被老爸发现先训了我半天,然后又帮我向妈妈掩饰,说是他尝尝有没有味道。这当然瞒不过妈妈,她又提醒我,热酱一搅会酸的。
有多种意外会导致酱变酸,完美的酱在几个年头里会出一次。品尝它的滋味已到秋季,盛一大勺放碗里,再用煮米水加至满碗,跟着米饭一起煮熟,今年的酱终于能吃到嘴了。
泡在焦黄的锅巴上,酱的浓郁香味盖过了每道菜。爸爸妈妈用筷子蘸蘸尝一口,厨师品鉴会就开始了:看吧,我说不能多放盐,现在味道是刚刚好;我就说要晒霉要多晒两天,还不够香……
我尝不出那么多,只觉得酱怎么吃都香,配上锅巴最香了。
成功的酱豆子会被妈妈分享给邻里,大家都知道今年我家的酱好,也知道谁家的酱今年又酸了,分别用的什么方法。每年都是这样,是晚间纳凉时亘古不变的话题。
酱豆子和人一样,一年又一年地奔赴夏天、等待秋天,根据温度、湿度的变化,缓慢发酵成长,最终不只是做成了酱,更像是一种七八月的背景,小乡村里的夏秋传承。
一家人一起做一件事。许多时候,就是这样的味道成为纽带,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