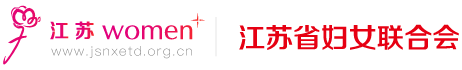我的家乡苏北平原一马平川。四五月,平原上涌动着一片金黄和碧绿。几乎是一夜之间,大地上纷纷支起一座座白色塑料薄膜覆盖的棉花营养钵苗床,如同碧绿深邃的湖泊上闪耀着白色的光亮。营养钵用制钵器一个一个打成,然后,人们在窨足水的营养钵里播下棉种,一个钵子里丢一到两粒棉籽,落种后支起竹架,再覆盖上塑料薄膜。棉籽破土发芽后,人们揭开薄膜给苗床通风、透光,棉苗叶片的嫩绿吱吱地绿了一层又绿了一层,闪烁着深绿色的光。
棉苗一天天壮实后,人们就要开始把带营养钵的棉苗移栽到地里,然后一遍遍地锄草、施肥、治虫、整枝、抹芽、打顶,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侍弄棉苗。直到棉花开花、结桃、吐絮、采摘,从初夏忙到深秋,每一棵棉花的叶片上,都滴着棉农亮晶晶的汗珠,甩落一地光芒。
盛夏,棉花枝叶挨挨挤挤,墨绿了大地,一直墨绿到遥远的天边。第一天开出的淡黄色的花,过了一夜后就变成水红色了。一场盆倒碗浇的雷阵雨后,干渴的棉花敞开喉咙咕噜咕噜地喝足了水,挺直躯干,舒展枝叶,叶片、花瓣上水珠滚落,精神抖擞。烈日画出棉叶的脉络,近乎透明,泛着一片银白的光。棉田里漂浮着闷热的气息。这时,若蹲在田边,似乎能听到棉花呼啦呼啦地舒展骨节疯狂生长的声音。粉色的花凋谢后,开始结桃。棉桃顶尖,很硬。一串串鸡蛋大的青色棉桃,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。
平原上的秋天是从棉桃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开始的。带着秋意的金风,吹过广袤的平原,也吹开了棉桃。褐色的棉壳龇牙咧嘴,喷吐出雪白的棉絮,开白了田野,开白了村庄。白色汹涌,构成了秋天平原的主色调。棉花白得圣洁,白得高贵,若雪,若银,似绒球,似笑脸,像云朵,像天使。从远处看,一望无际的棉田像覆盖了厚厚的白雪,又如蓝天上铺散的云朵,让人无法分清哪是天上跌落的白云,哪是地上盛开的棉花。大把大把金黄的野菊花,给雪白的棉田镶上了一道金灿的边。
棉农的笑脸如绽开的棉花,写满丰收的喜悦。大姑娘小媳妇头裹毛巾,腰系围腰,开始采棉花了。她们伸出三个指头撮住棉花,灵巧地往外一拽,棉花就从壳里整个摘出,手里抓满后再塞进围腰。莫言的小说《白棉花》中有一首《摘棉歌》:“八月里来八月八,姐妹们呀上坡摘棉花,眼前一片白花花,左右开弓大把抓,抓,抓,抓……”采棉的画面,差不多就如歌中唱的那样。阳光四散而去,凉露四聚而来,拾花一直拾到月光洒满大地。潮湿的棉叶闪烁着月光,洁白的棉花反射着月光,宁静的沟渠倒映着月光,带着寒意的露水凝重地打湿了棉花的枝叶和棉絮。蟋蟀尖细的叫声像泉水一样从草丛里渗出来,似乎在催促人们早点回家。拾棉花,得低头、弯腰,腰酸、胳膊疼,棉农们身子累,心里甜。
祖母摘回几只青桃,放在她房间的桌子上。不久,那几颗风干的棉桃裂开,祖母摘出棉花,用捻陀捻线。家中的花猫竖起双耳,惊奇地盯着祖母手中不停旋转的捻陀,好奇地伸出一只爪去拨弄捻陀,刚碰到便吓得退缩了回去。这场景,就像一幅画、一个镜头,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秋霜染红了狗骨树的叶子,红叶飘飘。带着霜意的寒风很快卷落了棉花的枯叶,寒霜扑打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棉花棵上,一些没来得及绽开的棉桃枯萎成了坚硬的僵桃。麦行中间的棉秆迎风而立,用它枯瘦如柴的身躯庇护着被寒风侵袭的麦苗,留下最后的风骨。母亲摘回发黑的僵硬棉桃,晒干后用方头木榔头一个个敲开,坐在点着煤油灯的饭桌旁摘出里面干硬的花瓣,打绒后与上等籽花掺和在一起,叫来弹棉花的师傅弹棉胎。哥哥结婚,母亲要准备几床舒适柔软的棉被;姐姐出嫁,两床鲜亮的红缎子棉被是必不可少的。
东北风刮得紧了,天说冷就冷了。母亲端出柳条针线匾,坐在桌边,套上针箍,从线板上抽出戳着的针,穿上线,开始为我们缝制棉袄、棉裤、棉鞋,让我们暖暖和和地过冬。俗话说,“千层单不如一层棉”,棉花吸收了阳光,柔软,厚实,温暖。冬天脚冷,母亲给我们的鞋里垫上一层棉花,就能从脚底一直暖到心里。母亲捻棉线,给姐姐织线衫,两根长长的毛线针在母亲灵巧的手中时而交叉,时而分开,像两只争斗的鸟。篮子里的白色线团调皮地滚动,一圈圈地变小。我们穿上带着灿灿阳光和母亲气息的棉衣、棉鞋,暖洋洋地去上学,滚雪球,打雪仗。天再冷,我们的心底都不冷。